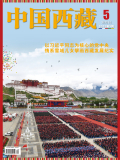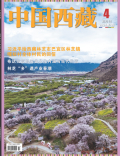每一個踏上通麥天險的人,無不心懷敬畏,這段八一與波密之間的路程共14公里,沿途山體脆弱,河流密布,一旦風雨交加,就可能引發泥石流,讓這條路被稱為“死亡路段”。不管是修建川藏線通麥路段還是維護該路段,都有英雄長眠于此。
但以旅人的角度來看,這里卻是另一番光景:一側山巒高聳,連綿不絕,山體植被茂密,云霧繚繞其間;另一側則是奔騰不息的河流,河水清澈見底,像一條靈動的絲帶穿梭在山水之間。如今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G318線波密至魯朗段改擴建工程已經完工,波密縣通麥鎮的項目部也已撤去,路面變得更加平整順滑,帕隆藏布似乎也變得更加溫存,路邊的防護欄等設施修葺一新,為行車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。
廚師陳雙才,便是項目部的一員。2001年,陳雙才聽從父親——一名老共產黨員的教誨進藏,親身經歷了西藏二十多年來發生的巨大變化,故事便從他入藏時講起……
五道崗
陳雙才拎著行李站在一條看不到盡頭的砂石路上,大口地喘著氣,似乎天地間只有他一個活物,藏羚羊呢,藏野驢呢,雪豹呢,牦牛呢,都沒見幾只。十幾個小時,窗外只有灰色的天和山脈,車兩側黃綠相間的斑駁草地不停變換。風摻雜著沙礫劈頭蓋臉地撲來,旁邊一家補胎店門口的鐵皮呼啦作響,泥土搭建的店鋪里也不知道有沒有人,陳雙才不得不側過身好讓自己呼吸順暢。
“要折返,你起碼到五道梁,再說,翻過唐古拉山,那可好多嘍,萬里長征剩幾百里,你要當逃兵嗦!”同行的乘客下車勸他。司機不停地按著喇叭催促,他剛同意了陳雙才下車的請求,路旁的補胎店有方便面火腿腸,可以歇腳。這位愛嘟囔的乘客可以在這等到回格爾木的班車,至于要多久,那就不關他的事了。
跟車的青海小伙下了車,吼道:“到底走不走!”陳雙才還是頭疼,卻突然冷靜了下來,從他家那個叫三合堰的小村子帶著幾十斤行李,坐三蹦子到市里、火車到西寧、大巴車離開格爾木、過了西大灘、到昆侖山口,幾千公里折騰到底是為了什么,他咬咬牙,把帆布包和蛇皮袋重新塞回車里——“忍一哈,堅持一哈,莫要拉稀擺帶!”陳雙才給自己打氣,重新爬回了各種氣味混雜的車廂。
車子一溜煙沒入了云端。司機和乘客閑聊:“‘到了五道梁,哭爹又喊娘’——五道梁都過了,再下唐古拉山就好多了。”陳雙才忍住劇烈的頭痛,想分散下注意力,他打聽藏羚羊去哪了,是不是讓偷獵分子捕殺了。
“他們(指偷獵藏羚羊的不法分子)都進去了,羊子有哩,等一會兒。”司機灌了口茶。
不一會兒,陳雙才看到了藏羚羊。接著,藏野驢、成群的牦牛、晶瑩剔透的流水似乎商量好地接踵而至,陳雙才覺得清醒了許多,在沱沱河堵車時甚至下車抽了根煙。
“當時對西藏心里還是有一種恐懼感,有點怕,路上一瓶礦泉水至少要十元,有的地方更貴,我買了幾個他們叫撒子‘焪鍋’的大饃,喝一口水,吃一口饃,饃帶到拉薩吃了幾天才吃完。”
“堅持一哈嘛。”陳雙才習慣性地往圍裙上抹了抹手。
陳雙才1966年出生,屬馬,身形削瘦,說話時專注地看著我,仿佛往人心里灌輸一種無聲但堅韌的力量。他第一次進藏時,兒子陳虎在四川崇州市公議鄉三合堰村上五年級,第二年陳虎的母親也動身前往拉薩。
啤酒之爭
起初,“西藏新人”陳雙才是來做酒水生意的。當時拉薩銷量最好的是黃河啤酒,這些啤酒從青藏線運來,再裝到人力三輪車摞個幾十箱送往拉薩各個店鋪、小賣部,貨運站常常呈現出一幅游擊隊四處出擊的場面。拉薩啤酒在迎頭趕上,雪花啤酒鋪天蓋地的營銷廣告也是山雨欲來,至于市中心的酒吧、朗瑪廳,則是百威和嘉士伯的地盤。
“黃河啤酒粗獷一點,有一點酸,不是很苦,入口后會再回甘,生津。像是在沙漠中渴了好久喝的第一口水,很獨特,這是西北的風格,但滿大街的火鍋店、川菜館越開越多,運費人工都漲,‘黃河’不行嘍,我們重慶山城啤酒度數低點,清爽、巴適,我打算分一杯羹。”
“啤酒買賣是一個具有消費慣性、大品牌壟斷、當地品牌也深度參與的生意,外來品牌初次進入打開市場十分不易,重慶啤酒靠的是老鄉人脈。”
陳雙才一共做了七年的酒水渠道供貨商。開始時各處跑,從酒吧、小店到燒烤攤,和服務員數啤酒蓋算錢,下午晚上守在飯館門前等著給老板推銷重慶啤酒。
“小區里的超市好一些,顧客比較穩定,老板進我的啤酒價格更低,要么進夠多少就送東西、降價,只要進去就能逐漸加大我的出貨量和陳列量。”
“再一個,有些歪的招。比如,有的人和收廢品的談,只收他的瓶瓶兒,別的不管。只要錢到位,滿足了收廢品利益需求,結果就是,別家的空瓶瓶兒沒人收,夏天一放,那味道相當難聞,而且占地方,你說老板撒子心情。”
“歪招還不少,我沒這樣干過哈,因為不是長久之計,但你做這行要曉得嘛,免得著了別人的道。”陳雙才說。
靠著積攢的口碑和人脈,陳雙才賺了一些錢,后來也做過白酒,但問題隨之而來,鋪貨量越來越大,需要自己墊付的資金也越來越多。有次輕信于人,合作伙伴信誓旦旦讓陳雙才第二天去結貨款,結果等他去時卻已經人去樓空。
“生意起伏不定,那段時間經常失眠。”陳雙才說道。
“最牽心的還是娃兒。”陳虎漸漸長大,別的父母對孩子守護陪伴,勞心勞力,陳雙才夫妻二人家長會一次未參加不說,就連兒子中考也不在他身邊,最長的一次甚至和兒子三年未見。陳雙才聽到的一個詞:“叛逆期”,這讓他心緒不寧。
“陳虎學壞了怎么辦?”陳雙才更睡不著了。
“我五年級時,父母便去了拉薩,我和爺爺奶奶在一起生活、過年。一年甚至幾年不見父母,似乎已經習慣了,見到時反而沒那么激動。”陳虎說。
“小姨和姨夫也在西藏務工,他們每年過年會回來,分開時表弟痛哭流涕,把充電器什么的藏起來,阻止他們離開,我覺得很幼稚。”陳虎有點靦腆地說。
陳虎初中畢業時,他想來西藏看父母,青藏線路上時間長,陳雙才不放心,警告陳虎不要獨自前來。陳虎便去打工,發傳單、賣竹筍,人生中第一次掙到了錢,給父母買了四雙鞋寄到了西藏。陳雙才聽著電話那頭,兒子講老板怎么罵他,心如刀割。
2008年春節,陳雙才夫妻二人回家過年,本打算過完年之后返藏清一清生意賬目。然而春節后,喧囂褪去,陳雙才審視著長大了不少的兒子,這時陳虎即將從懷遠鎮重點高中畢業,每晚學習到深夜,做高考前最后的沖刺。陳雙才決定暫緩入藏,陪兒子一起準備參加高考。
天路烹飪
2006年,陳虎讀高一,青藏鐵路開通了。暑假,陳虎從成都坐火車到拉薩,近五十個小時的硬座,陳虎腳都腫了。一下火車,母親便將他接回家,一家三口終于在拉薩團聚了。
陳雙才堅持自己動手做飯。不忙的時候,家里就是陳雙才主廚,他做的飯菜在老鄉、朋友圈小有名氣,何況這是兒子第一次來拉薩。陳雙才撈出鹵好的鴨掌、豬耳朵、肘子等,取出發好的魷魚和當時拉薩市面少見的海參,便開始忙碌起來。出租房充滿炒豆瓣醬的香味,小圓桌上擺滿了各色碗碟,一家人其樂融融地在一起吃了在拉薩的第一頓團圓飯。
陳虎開心地說道:“能天天吃到爸爸做的飯就好了。”
三年后,陳虎考入四川信息職業技術學院。陳雙才如釋重負,決定放棄酒水生意,從事自己一直喜歡的廚師行業。
2009年,陳雙才經朋友介紹來到了G317線夏曲卡至那曲公路整治改建工程B標項目部,負責三十多人的伙食。
在這里,陳雙才感受到:這里似乎沒有空氣的存在,天藍得讓人心顫,縱橫交錯的溪水下草根晃動、泥土清晰可見,光線一直透到水底。尼瑪縣孔瑪鄉,海拔4580米,比拉薩高一千米左右,水燒開只需要八十多度,他不知道要在這里待多久。
陳雙才剛到便參與了一場小規模救援行動。“剛去的那天天氣是假象,第二天下午瀝青拌合站的帳篷就讓大雪壓塌了,我就曉得事情沒有那么簡單。”項目部的人七手八腳掀開帳篷一角,把埋著的人一個個拉出來,大家大口喘著粗氣,嘴唇都是青紫色的。
“要穩扎穩打,最重要的是保證干凈的水、燃料和食材。”陳雙才每天和徒弟們開一輛銹跡斑斑的皮卡,車廂里放著三個大鐵桶,去十幾里外一條稍寬的溪流拉水。冬天把冰面鑿開,撈起透亮的冰塊,有半尺厚。
“物資就是這么短缺,帶蓋的塑料桶都沒得,拉回來的水灑一半,再沉淀一夜,第二天才能用。”
陳雙才又修整了一架不知道哪來的小推車,找人焊接一番,一有空就去撿牛糞,因為不知道哪天會大雪封路,氣罐車有時走到一半只有折返回去,液化氣很難保證穩定供給。
“草原你看起來是平的,其實都是一個鼓包一個鼓包的,大包接小包,車子在上面過山車一樣,我的小推車也和皮卡車拉水一樣,不能太滿,要不牛糞都灑嘍。”
談起廚師工作,陳雙才如數家珍。
“做菜嘛,要保證衛生,營養和口感,不像大飯店里那么精致賣相好,但吃得一定要衛生、舒服。”
陳雙才說,那曲鼠害較重,老鼠不僅侵蝕草場,有的甚至在人的眼皮下大肆啃食食材,有時進門,一跺腳,就有老鼠四下逃竄。
“食堂肯定是重災區,但我后來采取了一些辦法還是管用的。”
起初,陳雙才用木架把食材架起來,將四個腳撐抹上黃油并放進水桶里,設想中老鼠不僅爬不上去,還會一呲溜掉進水桶。但老鼠能“上天入地”,陳雙才有次看見老鼠在桶里游了個泳,沾點水蹭著黃油繼續往上爬。
后來,陳雙才托人從拉薩帶回來了一種細鋼砂網,不銹鋼制成,價格不菲,四塊勾連焊接在一起掏出小門,組成一個小型的鋼籠,把食材裝進去架起來,從而隔絕了鼠害。
“菜品質量也要穩定,不能由著性子來,比如你今天心情好,精雕細琢一大桌,哪天又胡搞一番,這樣大家就會有意見。說實話,在那個地方,睡覺都不一定睡得好,一天最大的享受便是吃飯。”
慢慢地,陳雙才學會了辨別蟲草,偶然得到一兩根,放進稀飯里。項目部的人圍觀蟲草稀飯,都驚訝不已。
三代傳承
陳雙才問,流動黨員是什么意思,在哪交黨費,現在入黨需要什么流程等。原來陳雙才的父親是一名老共產黨員,以前做過三合堰村大隊長,生前就鼓勵陳雙才到西藏去,希望他扎根高原邊陲干出一番成績。在那曲的第三年,老父親病危,陳雙才連忙請假,回去守在床前一個月盡孝直至送終。
2021年,兒子陳虎也加入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,目前在西藏天路(林芝)代建辦,負責工程項目的前置手續。
“以后能天天吃到爸爸做的飯就好了。”多年后,陳虎如愿以償。但是,2018年就已入藏工作的他還是和陳雙才聚少離多,這也是工程人的常態。
但是,陳虎說:“再也不用像第一次來拉薩,分別時在站臺強忍淚水。那時,火車啟動后,轉頭看車窗外,父母在抹眼淚,卻越來越遠,只聽見車廂里嘈雜的聲音,那個感覺太難受了。”
2024年8月19日傍晚,海拔2200米左右的西藏林芝通麥鎮,曾經的藏建·天路波魯項目部的工程已經完工。在茫茫雪山和綠色山林環繞下,新修的公路像一條絲帶蜿蜒,陳雙才故地重游,在視頻里逗弄著剛上小學的孫兒。他說,現在家里是四世同堂,視頻里幾個老太太搓著麻將,精神矍鑠,看著喜慶極了。
“川藏鐵路一通,相關公路配套設施完善,回家只要幾個小時。”
“陳虎他們現在吃點苦,難一點,修好了不得用上幾百年。”
陳雙才平時話不多,今天也高興地打開了話匣子。
陳虎說,這里就是家。此心安處是吾鄉,“建設美麗幸福西藏、共圓偉大復興夢想”不僅僅是一句標語,而是許多活生生的人們通宵達旦、熱火朝天的真實寫照。身處舉世矚目的“世界屋脊”,西藏的發展天翻地覆,面貌改天換地,人民生活今非昔比,實現了跨越上千年的滄桑巨變。如今的西藏,原野千里,處處生機勃勃;高山大川,一派欣欣向榮。
這離不開陳雙才父子這樣的普通建設者的辛勤付出,他們二十多年的經歷,無不表露著一種中華民族的共性——堅韌、感恩和積極樂觀的奮斗精神:拿起廚具(熱愛的事業)便是生路;遇到挫折困難,不會怨天尤人,而是迎難而上想辦法克服;在工作生活中與當地百姓交往交流交融;為了子女的教育成長付出辛勞;孩子長大后也義無反顧進藏……他們來自五湖四海,操著不同的口音,奔波扎根于西藏,以實際行動匯聚成建設西藏的磅礴力量。